作为一个支持MeToo的乖乖女,我竟然从强奸幻想中得到快感?
2021-01-24 16:05:38
“你刚刚的表情好痛苦啊,我弄疼你了吗?”一番云翻雨覆之后的例行复盘过程中,男票这样问我。
“啊?”我倒是记不得刚刚有什么伤痛,甚至比以往更加愉悦那么一点点。
“不对,你刚刚真的看起来不太舒服,眉毛眼睛全挤在一起了。以前不是的。”男票盯着我,“说真的,我是不是把你弄疼了?我这次的确有点粗暴了。”
我回敬给他一个同样迷惑的眼神,“可能因为我GC了。”
“啊?!”他似乎对自己的“粗暴”带来了我的快感而不解。但是说真的,我还挺享受这种被强迫的感觉——换言之,我刚刚刻意地放松了自己的一切动作,把身体全权交给他,就仿佛——他在强奸我。

我很难向他说出当时的想法,这听起来并不是合理的GC获得路径。但对暴力和压迫的性幻想的确在我的脑海里根植已久。从少年时代同学之间广为流传的言情小说开始,虽然我对女主能够被霸道总裁毫无理由地喜欢这一点颇为嗤之以鼻,却总会被那些极具挑逗性的捏起下巴或者壁咚瞬间吸引,那些瞬间往往是小说里最能让我产生代入感和引发后续联想的……
最初我只是在梦里把自己代入小说情节,幻想来自一个优秀帅气的异性的“压迫”;到中学时代,我开始会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明目张胆”地一边DIY一边做着我的白日梦,仅存在于想象中的身体失控弥补了那时候DIY手法的不足,我的大脑已经能让我自己经历过无数次“小豆豆”都没体验到的GC。
梦里不知身是客,当那一晌贪欢的快感逐渐消失时,取而代之的是强烈的羞耻与自责。中学时的我已经开始接触性别平权,每每读到熟人性骚扰的案例总会愤懑不平。
强奸?我在每周随笔里写过无数次对强奸者绳之以法、强奸受害者勇敢举报的重要性。这个词无论如何也不应该与愉悦联系起来:现实里的强奸给多少人带来了苦痛,而我怎还能期待。
所以我根本不敢和任何人倾诉自己的快感与快感结束时的愧疚。没有人会想到,这个表面上看起来不网聊不早恋、支持Metoo的乖乖女,背地里会用如此龌龊的方式探索身体?

高三最后的繁忙学业让我暂时忘记了这件事。而到了大学时,对胁迫、猥亵、乃至强奸的想象之频繁愈发不可收拾。作为法学生的我白天坐在课堂上讨论着自由平等,半夜却躲在寝室窗帘后用一场听起来像是臣服于男权的幻想配合手指动作来释放身体里蠢蠢欲动的荷尔蒙。
再到后来便是和男朋友滚床单假装自己在经历一场强暴。我的理智告诉自己千不该万不该,不该将身体的掌控大权交给他人;而身体对快感的渴望却诱惑着我一次又一次地在想象中构造一个让我欲火焚身的霸总。
某一天,我突然在网上看到一个女性说自己常常幻想自己被强奸,对此感到深深羞耻,却又欲罢不能。
这说的不就是我吗!
在那之前我一直以为“性幻想”只适用于对具体性行为对象的幻想,譬如清晨和某个男明星在同一张床榻上醒来、譬如隔壁班打篮球超好的男孩拥你入怀。但我在搜索引擎里敲下“强奸”和“性幻想”这两个词后,逐渐明白“性幻想”也可以是不具有实体容貌的——正如我对具有强迫性质的性行为的幻想,我只能想出一个场景,以及一个广义上的高大帅气的“施暴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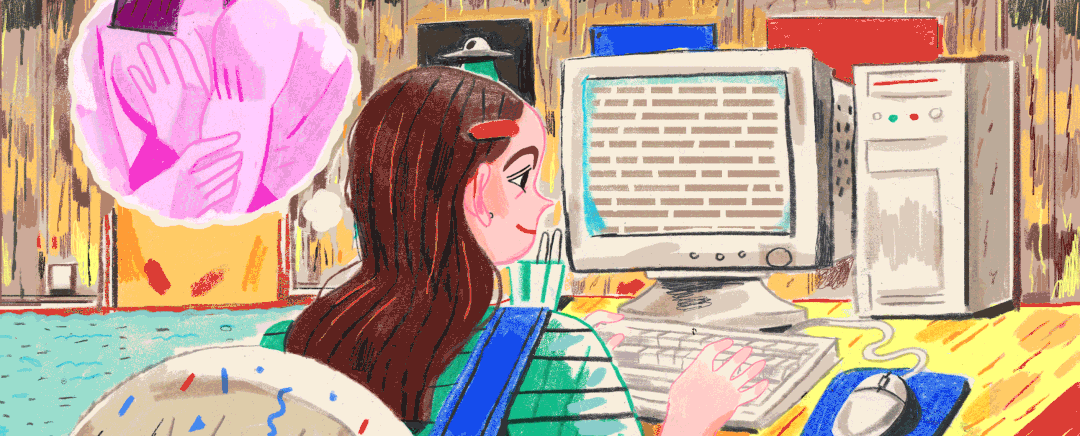
这个被称作rape fantasy的奇特幻想模式早在上世纪就已经被心理学博士Louis Janda(1985)指出,对于强奸行为的幻想在女性的性幻想之中最为常见;2009年一项针对美国西南部某两所大学本科女生的调查表明(Bivona&Critelli,2009),这355位绝大多数年龄在18到21岁的女孩中有62%的人曾有过强奸幻想,实验者们还认为考虑到受访者羞于启齿的心态,实际数字或许比这个更高。
那我可放心了,原来不止我一个人会这么幻想。然而——为什么我这样一个新时代独立女性会在脑海里给自己安排个屈服于男性的角色?
再度检索,我发现关于强奸幻想的产生原因解释众说纷纭,或是为了减轻“性行为带来的负罪感”,或是源自于女孩在有性经历前接触到的情色作品多为男本位,又或是最近几年的主流看法:高敏感、性观念开放的女孩才会产生强奸幻想,因为学者们认为性压抑的女孩“不常有性幻想”。(Shulman & Horne,2006)
照这么说来,我其实还算是个性观念比较开放的人?

在我回忆曾经的幻想经历以及查阅到的资料时,男票和我大眼瞪小眼地在床上坐着,他还在迷惑究竟是什么给我带来了GC,而我在犹豫要不要把刚刚的想法以及我从小到大经历过的这种强奸幻想描述给他听。
“所以说……你喜欢我粗暴一点?”谢天谢地,他终于打破了这尴尬的沉默。“其实我在幻想被强奸。”我脱口而出。
男票的反应倒是出乎我意料。他长舒一口气,说“那咱多玩点dirty talk不就行了?可你刚刚也一句话都不说,吓得我以为把你弄伤了。”
“我觉得这种想法太羞耻了。”我大概有些面红耳赤。
“这有什么,幻想而已,你又不会真的希望被强奸。”
是的,我绝不会希望在现实中被强奸,我也坚决地反对现实中任何形式的性暴力,当一方仗着自己的体能或者权势优势侵犯另一方时,受害者所面临的不可选择、无法逃脱也就意味着ta性的权利乃至人权的部分丧失。
但幻想不同,我脑子里的幻想完完全全地在我的控制范围内,那令我感到兴奋的所谓“强奸”以及所谓“反抗”不过是我跳脱的思绪给自己加的戏,它依然服从着一个深处的根本原则:这是一段双方自愿的性行为。
或许正是因为幻想和现实的严格界限,女权主义作者Susie Bright认为“强奸幻想”应当更名为“con-non-con play”(意为“双方同意的不同意”),我深以为然。










